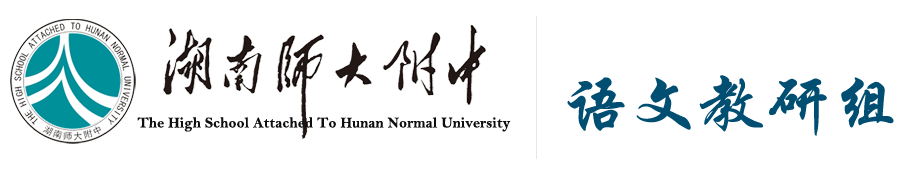李商隱閱讀資料
發布:語文教研組 來源:未知 日期:2019-03-21 人氣:
公元812年,在河南省獲嘉縣縣衙的府第內,李商隱誕生了。父親李嗣正任獲嘉縣縣令。三年后,李嗣受聘為浙東觀察使幕僚。李商隱的童年時代便在獲嘉至江浙一帶度過的。李商隱注定是一個悲情的詩人,李家從商隱曾祖父起,一連幾代都過早病故。終于,在商隱十歲時,父親在幕僚任上過逝了。孤兒寡母扶喪北回鄭州,由于多年未回故鄉,雖在故土,卻情同外來的逃荒者。李商隱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就寫道:“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祭裴氏姊文》)。或者正是由于家世的孤苦不幸,加之瘦羸文弱,形成李商隱易于感傷的性格,但同時也促使他謀求通過科舉,振興家道。
公元829年,也就是唐文宗太和三年,李商隱離開了自己的家鄉,來到長安,謁見了當時朝廷里的權貴令狐楚,很受賞識。令狐楚將他聘入幕府,李商隱開始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幕僚生活。其間,令狐楚親自指點李商隱,教他寫今體文。
李商隱二十三歲那年,公元835年,李商隱上玉陽山東峰學道。而玉陽山西峰的靈都觀里,他邂逅了侍奉公主的宮女宋華陽,宋年青美麗,聰慧多情,兩人很快雙雙墜入情網。兩個多月后,這段超出常規的愛戀,終因不為禮教和清規容許而豪無結果,短暫的歡娛,無望的永好,只在李商隱的心中留下了永遠的傷痛。李商隱一生中留下了眾多的《無題》詩,而最為人們所知,也最蕩心動魄的《無題二首》即完成于此時。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
曉鏡但愁云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燭紅。嗟余聽鼓應官去,走馬蘭臺類轉蓬。
玉谿生的這首《無題》,全以首句“別”字為通篇主眼。江淹《別賦 》說:“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 “黯然”二字,也正是玉谿生此詩所表達的整個情懷與氣氛。在古代,即使是盛唐這樣一個繁華的朝代,音信依然是不便的,于是出門在外,情人分離就釀成了濃濃的情思,更何況李商隱這時的這種情思并不僅僅是距離的遠隔,死別是痛苦的,而生離卻更勝死別。于是李商隱張口一吐便出了“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的千古名句。春蠶自縛,滿腹情絲,生為盡吐;吐之既盡,命亦隨亡。絳蠟自煎,一腔熱淚,淚而長流;流之既干,身亦成燼。
然而,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都是昨日舊事,“曉鏡但愁云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一個“改”字,傳達出的是青春不再,逝水常東的悄然心驚。其苦情蜜意,全從一個“改”字傳出。而“寒”字也是苦心營造的,此寒,如謂為“心境”所造,月光本無所謂冷暖,但在作者眼中,滿眼盡是離情別緒,因此,看到的月光,也便寒冷了。李商隱到了晚年,還設法在長安約見了宋華陽。
公元837年,在令狐楚的兒子令狐陶的幫助下,李商隱進士及第,但也就是這一年的年底,令狐楚病逝了。李商隱一生的悲劇從這一年正式拉開了帷幕。
第二年的春天,李商隱投奔了涇原節度使王茂元,當了幕僚。王茂元愛商隱之才,將最小的女兒嫁給他。這時,李商隱26歲,婚后感情很好。李商隱有一首思念愛妻的《夜雨寄北》,仍然為現代人稱道,亦為之辛酸。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 何當共翦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當時朝廷內部的朋黨斗爭十分激烈,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和以牛僧儒為首的牛黨史朝廷里的兩大對立的勢力。令狐楚父子為牛黨要員,王茂元被視為親近李黨的武人。李商隱轉依王茂元,在牛黨眼里是“背恩”的行為,從此令狐家的人對李商隱不滿。黨人的成見,加以李商隱個性孤傲,他一直沉淪下僚,在朝廷僅任九品的秘書省校書郎、正字,和閑冷的六品太學博士。為時都很短。從大和三年踏入仕途,到大中十二年去世,30年中有20年輾轉于各處幕府。東到兗州,北到涇州,南到桂林,西到梓州,遠離家室,飄泊異地。
李商隱最后一次到梓州作長達五年的幕僚之前,妻子王氏又不幸病故,子女寄居長安,這就更加重了精神痛苦。李商隱寫了一些詩懷念她:
《落花》
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參差連曲陌,迢遞送斜暉。
腸斷未忍掃,眼穿仍欲稀。芳心向春盡,所得是沾衣。
“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所深愛的人走了,花園里花瓣四處飄飛。一個“亂”字,把作者的心情和自然景象有機的組合。廝守多年,原盼著白頭偕老,但佳人卻先于自己撒手西去,這如何令作者不心亂。“參差連曲陌,迢遞送斜暉”兩局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寫落花亂飛的情狀。前者著眼于空間,寫落花無處不在;后者從時間寫,落花連綿不斷,無盡無休。不僅如此,關鍵在“斜暉”二字,夕陽西朝下的落花,更表現了詩人傷心,煩亂的感受。
逢著美景良辰,則懷念當時歡愛,而無時無刻不悲悼,見一花一草也要寓意興悲,自此以后,李商隱每逢七夕必有一詩。李商隱還有一 首七夕那天寫的《曼倩辭》也是悼念亡妻的佳作:
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間。如何漢殿穿針夜,又向窗中覷阿環?
在李商隱生命的最后一年,也就是他46歲的時候,他寫下了一生當中最重要的一首詩,也是最難懂的一首詩,卻又是后世讀詩之人最喜歡讀的一首,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學的《錦瑟》。
李商隱雖然在他短暫的四十六年的人生歷程中仕途一直不得志。但他依然是一位關心現實和國家命運的詩人,他的各類政治詩不下百首,在其現存的約六百首詩中,占了六分之一,比重相當高,表現了李商隱積極的用世精神。
李商隱作了涇元節度使王茂元的幕僚和女婿后,在開成三年(838),商隱赴京應博學宏詞科試,落選后回到安定,也就是涇州,登上了城樓有感,寫下了千古流傳的遣懷詩《安定城樓》:
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盡汀州。賈生年少虛垂涕,王粲春來更遠游。
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雛竟未休。
這首詩頸聯寫得最好。從詩歌中,我們讀出了作者既恬淡的心情,又有擔當事業的志氣。首二句寫景,即景所以生情,以下六句的豪情壯志、無窮感慨都由此生發。三、四句先以兩位古人自比。賈誼獻策之日,王粲作賦之年,都與作者一般年輕。賈誼上《治安策》,不為漢文帝所采納,作者應博學宏詞科試而名落孫山,其心境與賈誼上書未售,同樣縈紆抑郁。王粲避亂至荊州,依劉表;作者赴涇州,入王茂元幕,都屬寄人籬下。用兩位古人的古事,比自己當前的處境和心情,取擬于倫,十分貼切。五、六句抒露志趣和抱負。作者的遭遇雖然困頓,可是他的凌云之志,未稍減損。江湖、扁舟乃使用春秋時代范蠡的典故;范蠡佐越王勾踐,“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見《史記·貨殖列傳》)。意謂,自己早有歸隱江湖之志,但等回天撼地之日,旋乾轉坤之時,頭飄白發,身入扁舟。永憶江湖,即懷淡于名利之心;欲回天地,即抱建立功業之志。兩者似相反,實相成。這兩句詩,既灑脫,又遒勁。這兩句詩反映了封建社會里才志之士的積極向上思想,既懷著恬淡的心情,又有擔當事業的志氣。七、八句借莊子寓言表示自己敝履功名利祿,正告他人不要妄加猜測。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于南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于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秋水》)。這兩句詩,既闡明自己沒有患得患失的私心雜念,胸次光明磊落,淡泊寧靜,為上面“永憶江湖”句提供有力的論證;又表示對世間一切惡濁事物,睥睨蔑視,決不妥協容忍;還尖銳地批判那些捧住權位不放的祿蠹,對他們盡調侃奚落的能事。據近人張采田《玉溪生年譜會箋》,作者應博學宏詞試被擯,是由于牛黨的打擊,誠如是,這句詩乃是有的放矢的。唐代后期,許多皇帝不重求賢重求仙,希企長生。李商隱一再予以冷嘲熱諷。《賈生》:“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借賈誼宣室夜召一事,加以發揮,發泄了對于皇帝不識賢任能的不滿。賈誼貶長沙,久已成為詩人們抒寫不遇之感的熟濫題材。作者獨辟蹊徑,特意選取賈誼自長沙召回,宣室夜對的情節作為詩材。《史記·屈賈列傳》載:賈生征見。孝文帝方受厘(剛舉行過祭祀,接受神的福佑),坐宣室(未央宮前殿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對方)。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在一般封建文人心目中,這大概是值得大加渲染的君臣遇合盛事。但詩人卻獨具只眼,抓住不為人們所注意的“問鬼神”之事,翻出了一段新警透辟、發人深省的詩的議論。
安史亂后,唐王朝由極盛走向衰敗,李商隱對玄宗的失政特別感到痛心,諷刺也特別尖銳。如我們這課要學習的《馬嵬》:
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聞虎旅傳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
詩中每一聯都包含鮮明的對照,再輔以虛字的抑揚,在冷諷的同時,寓有深沉的感慨。
怎樣讀李商隱詩
余恕誠
唐代詩壇,名家名作極多。即使一般讀者皆能背得好多佳句的詩人,放在那一溜長長的名單中,位次也未必很前。李商隱如何呢?清代吳喬《西昆發微序》說:“唐人能自辟宇宙者,惟李、杜、昌黎、義山。”著眼于詩的創新精神,把他放在能自辟天地的大作家之列。葉燮《原詩》說:“李商隱七絕,寄托深而措辭婉,實可空百代,無其匹也。”雖只限絕句,且揚之過高,但亦可見李商隱在其心目中的地位。清代最具有普及性的詩選本《唐詩三百首》,選商隱詩24首,篇數僅少于杜甫、王維、李白三家。這個“訓蒙”讀物編選的依據是“專就唐詩膾炙人口之作,擇其尤要者”,于此,亦可見李商隱詩的可讀性及其流傳程度。
……
李商隱的詩歌有寄托遙深、構思細密、表現婉曲、情韻優美、語言清麗、韻律和諧、工于比興、巧于用典等一系列優點。由這些方面合成的總體風貌,在詩壇上是以新的姿態出現的。他在寫法上頗有一些異于傳統之處:(一)以心象融鑄物象。晚唐社會的種種變態,特別是它的厄塞、衰頹,使得像李商隱這樣一些失意文士,由沮喪、失望轉向追求主觀心靈,內心體驗往往比他們對外物的感受更加深入細膩。當心靈受到外界觸動時,會出現一串串心象序列,發而為詩,則可能以心象融鑄眼前或來源于記憶與想象而得的物象,構成一種印象色彩很濃的藝術形象。李商隱處境又很惡劣,心事往往鉗口難言,于是在潛心摹寫心象的同時,又須著意將其客觀化,借客觀物象經過改造之后可以誘發多種聯想的優長,將本難直接表現的心象,滲透或依附于物象之中,令人撫玩無、聯類興感。如詠蟬曰“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表現的是作者羈役幕府、心力交瘁、舉國無親的那種“冷極幻極”的心象。“一春夢雨長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寫的是圣女祠,而詩人種種幻滅的心象也正如夢雨靈風之恍惚。這樣以心象融合客觀世界某些景象或事物鑄造形象,對傳統情景交融手法是一種突破。(二)比興寄托和象征的融合。比興、象征作為兩種相關而不相同的藝術手法,本不一定聯合運用,它們和寄托更未必直接聯系。李商隱的詩歌由于在內容上側重表達人生的體驗與感受,藝術上追求心象與物象的統一,靠一般明顯的比喻,每每不足以充分而有效地表達,遂常用象征性的表現手法,并進而將比興與象征融合起來。比如“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無題》),“金燼暗”“石榴紅”除渲染氣氛、點明時節外,前者還可以作為無望的相思的象征,后者則暗示青春年華的流逝。又如“江風揚浪動云根,重碇危檣白日昏”(《贈劉司戶蕡》),描寫江風鼓浪、山搖石動、危舟獨系、天昏地暗的景象,同時又兼含比興象征,將“當日北司專恣,威柄凌夷,一齊寫出”(《李義山詩解》)。《錦瑟》中間四句可能每一句都有象征意味,而且基于詩人內心的恍惚迷惘,所象征的內容還帶有豐富性和不確定性,意象的暗示性大大增強,迷離深隱,意蘊多重。(三)追求朦朧凄艷的詩美。將復雜的矛盾,甚至惆悵莫名的情緒,借助詩心的巧妙生發,鑄造成如霧里繁花的朦朧詩境,是李商隱畢生加以追求的目標。而像“楓樹夜猿愁自斷,女蘿山鬼語相邀”(《楚宮》);“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春雨》);“玉盤迸淚傷心數,錦瑟驚弦破夢頻”(《回中牡丹為雨所敗二首》其二);“微生盡戀人間樂,只有襄王憶夢中”(《過楚宮》)一類名句,以及《無題》《錦瑟》等篇,都達到了這一境界。這種詩美主要構成因素是朦朧、瑰麗、感傷。商隱感于時代的沒落、身世的不幸,有一種固結不解、惆悵莫名的哀傷情緒,“此情可待成迫憶,只是當時已惘然”(《錦瑟》)。當把這種情緒注入本已融合了心象與物象、比興與象征的詩境時,各種因素互相交匯、層層掩映,真有“絮亂絲繁天亦迷”(《燕臺詩四首·春》)之感。上述三個方面,說明李商隱詩歌的藝術手段、追求目標與傳統不同,詩境亦深隱朦朧。把李商隱詩當作“邪思”的產物,認為會壞人心術,固然是像面對一位出群的美人,口稱“尤物”,不敢正視一樣可笑。但如果是抱另一種態度,想要接近她、認識她又該怎么辦呢?我認為可以區分不同情況,采取不同方式、步驟。李商隱集中一部分像《夜雨寄北》那樣清新流暢的作品,固然不存在閱讀的障礙,就是那些批評時政、反映現實的詩,由于比較質實,只要掌握背景,弄懂語言和典故,也不難領會意旨所在。其難解之作,如無題、詠物之類,最主要的難點是不易參透詞語典故外殼下所包含的情思。對此,讀者既可以不求甚解,也可以通過知人論世等途徑作更深入的探求。李商隱的詩,除少數學李賀詩體者外,多數詩脈暢通,由語意、聲韻所傳達的總體情緒氣氛并不難于感受。無題詩一般用典不多,語言清麗,盡管細心探尋時會感到閃爍迷離,但愛情描寫本身尚不晦澀。即使是《錦瑟》,像“滄海月明珠有淚”,寫月夜滄海之中,明珠晶瑩閃爍,盈盈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寫暖日照臨,地中良玉,蘊發縷縷云煙。這些喻象,是無論對詩旨作何種詮釋,都必須以之為依歸的。為求省便的讀者,似可不去追究其中的埋伏,僅僅接受語言媒介給予的直覺形象和情緒,也未始不是一種藝術享受。《唐詩三百首》本屬啟蒙讀物,選了《錦瑟》和五首《無題》詩,選家豈能指望學童領略多少深意?不過供其讀讀背背而已。梁啟超說:“義山的《錦瑟》《碧城》《圣女祠》等詩,講什么我理會不著。……但我覺得他美,讀起來令我精神上得一種新鮮的愉快。須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現的情感》)可見讀李商隱詩,不求甚解不失為一法。有人想再前進一步,對詩旨把握得切實一些,則可求助于注本和選本。“文革”后,李商隱詩的研究成為熱門課題,近年出版的一些注本和選本,持論一般都比較切實、審慎,可資參考。至于想做更深入的推究探尋,有所創獲,則應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把握詩歌整體,注重實證,避免臆測。在內證與外證不足的情況下,寧可理解得虛涵一些,也不要僅據片言只語去比附。另外,李詩由于注意表現心理意緒,又常常捕捉瞬息間的印象,多用象征手法,在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運用西方理論研究中國詩者,很容易取之作為剖析對象,這會有助于對李商隱詩歌認識的深化,開拓新的局面,但正因為是開拓,難度較大,尤須堅持科學的精神。加拿大籍華裔學者葉嘉瑩先生曾強調從事這類工作既需要對中國舊詩具備足夠的修養,又要對西方文藝理論有深刻的認識和了解(《關于評說中國舊詩的幾個問題》),這種意見我們應該重視和聽取。
(節選自余恕誠著《唐音宋韻》)
品讀李商隱
胡晶華
每當被人問起“人活著為什么”這一類的問題時,我總是笑而不答,把話題轉移。從學校出來踏入社會已有些年,這中間經歷了一些事情、一些波折,照常人看來再遇到事本該會從容應對,談笑自若,寵辱不驚。可我非但沒有修煉到這一境界,有時反而對許多事更加惶惑與迷茫了。夜半醒來,黑暗中枯坐,覺得命運之神有時也太狡詐殘酷了,常在你猝不及防的情況下,突然扯下歌舞升平的偽裝之幕,把社會與人性的卑劣與丑陋直推到你面前。而你盡管一千個一萬個不情愿,也只能默默接受這份“饋贈”,沒有任何別的辦法。但過后肯定會忍不住問:這究竟是為什么?
千年前,一位詩人在死神敲門之前,也發出類似的感慨: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面對這首絕唱,許多人同我一樣,欣賞過后,卻不明白詩人究竟要向世人說些什么。李商隱,如同他這首“無端”又“惘然”的詩一樣,引發后世許多讀者、作家、文學評論家去猜測、辨別、破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再用荒疏已久的生澀之筆去寫點什么,無疑是可笑而不自量的。李商隱的品行直到現在還有爭議,其性格估計更是沒有幾個人喜歡。他自己曾感嘆“古來才命兩相妨”。是啊,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命運悲慘的作家,從屈原到曹雪芹,可以開列出一大串長長的名單。但是人家可并不都像你李商隱一樣,悲泣感傷,纏綿惶惑。陶淵明的達觀、隨遇而安;李白的笑傲權貴,倚劍長歌;蘇東坡的曠達與超然,都比李商隱這樣長期沉陷在悲觀心緒中不能自拔要灑脫而明智得多。與這述這些大作家相比,多愁善感的李商隱更接近一個純粹的詩人。他對于人間摯情摯愛拋不開,放不下,敏感又執著;明明看透看穿了一些東西,卻不便隨意發泄、而只能拼命壓抑的痛苦,在其他中國文人身上很少見到。而這種多少有些扭曲與偏執的心態,投射到詩作上,恰恰成就了李商隱,證明了李商隱!使我們看到了一個也許并不可愛,但卻絕對真實的唯一的李商隱,一個讓正統士大夫啐罵,讓志得意滿的成功文人嘲笑,被冷落了千年才穿過厚重的歷史積塵進入到我們視線的李商隱!
不知不覺間已寫到這兒了,真不知道再寫下去會是什么樣子。我想它應該不是傳記,不是小說,不是作品賞析,更不是網上流行的所謂“穿越”類文章,可能也只有等自己把這篇關于李商隱的“四不像”的東西真正寫完,才會看清它是什么。但這已經不重要。
我的兄弟,懷著你的愛和你的創造到你的孤獨里去;很久以后,正義才跟在你后面。這句話是被人長期誤解的德國哲學家尼采為一切創造者預言的命運。命運是什么?人的命運為何各不相同?對此,許多人喜歡引用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句話“性命即命運”為歷史人物的命運作出詮釋,包括孤獨的尼采,也包括我所喜愛的,在文學創作與藝術表現方面十分獨特,甚至在許多方面逸出常軌而難為常人所接受的晚唐大詩人李商隱。許多作家、評論家一提到李商隱,幾乎無一例外地將他的悲劇性格視為其一生悲劇命運的最主要原因。對此我們當然不可否定。可是,性格又是什么?每一個人剛出生時都不過是一張白紙,究竟是什么令這張白紙暈染鋪墊了一層濃重的悲情底色?這似乎又回到了本文的開頭,類似“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我不想在這里繞圈子。我是想,許多生命的誕生其實是無序的,被動的,強迫的,只因某個機緣才很偶然很慌亂地降臨到人間,降臨在某一時空下的區域內,某一區域內的家庭中,從此成了某對父母的子女,開始了在某種環境下的生活。我不知道這是否就是人們常說的命運,但從人出生開始,確實有許多事物不是自己所能掌控與選擇的。——父母是不能選擇的,家世是不能選擇的,民族是不能選擇的,時代是不能選擇的!而這些,對一個孩子早期氣質的形成,無疑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李商隱與李唐王朝的創立者同姓,會使人首先想到他是否與當時的皇族有某種聯系。對此李商隱曾在一首詩名很長的詩中不無自豪地宣稱“我系本王孫”,讓世人看到自己有個與唐皇室同宗的出身。然而標榜歸標榜,后人考證,其實商隱同李唐皇室的關系實際上非常疏遠,當朝的同姓著名詩人李白李賀等人也都有過類似的傲然宣稱,不足為憑。而商隱同李唐皇室的關系好像較李賀的家族世系還要遙遠許多。所以這個遙遠的皇室宗親關系,并不會給這位長期沉淪的詩人帶來任何政治、經濟上的實際利益。從商隱高祖、曾祖、祖父直到他的父親四代近世宗親的地位看,雖有官職,卻多為一些品極很低、權限很小的州縣官吏。應該說他是出身寒微的。
商隱的曾祖父李叔恒是位有才華的文人,年紀輕輕就進士及第,與當時劉長卿、劉若虛、張楚金等詩人齊名。可惜這個少年才俊不到三十就英年早逝,給李家沉重打擊。曾祖母盧氏夫人堅強地挑起家庭重擔,教育兒子李,也就是商隱的祖父。祖父也很爭氣,明經及第,被錄為官。但可景不長,不幸再次降臨到這位善良卻苦命的老婦人頭上,兒子也因病早早去世。中年喪夫,現在該享受天倫之樂的時候又喪子,這種打擊一般人是難以承受的。可這位堅強的老婦人強咽下淚水,又默默地擔負起撫育孤孫李嗣的重擔。而李嗣正是商隱的父親。商隱雖與自己這位曾祖母未曾謀面,但就是這位老婦人,在夫亡子喪、李家即將崩塌的危難時刻,艱辛撫養孫子李嗣長大成人,延續了書香之家的傳統門風,使李家不至門庭敗落,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位令人尊敬的老婦人是李商隱的生命之源,精神之源!
唐憲宗元和七年年初,河南懷州的獲嘉縣衙內,一個小生命的誕生給縣令李嗣帶來無限欣喜。李嗣已成家二十多年,生有三個女兒,卻還沒有一個兒子。他對這個跚跚而來的兒子自然無比珍愛,用秦末漢初隱于商山上四位高士的典故給孩子取名商隱,字義山,隱含著對這個孩子寄予厚望。
兩年后的秋天,李嗣在獲嘉縣令三年任期已滿,被新上任的浙東觀察使聘為幕佐,于是一家老小離開河南老家,來到風景秀麗的浙東。此時商隱應該已經開始記事了。早期的生活環境對一個人今后氣質的形成、品味情趣高下、人格修養也是一個重要影響方面。孟母三遷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江南不但風景秀麗,物產豐富,還有大量歷史沉淀的人文景觀掌故,已到了啟蒙之齡的商隱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開始接受到最初的教育。這一時期也是商隱一生中最幸福快樂的一段時光。雖然那時他的裴氏二姐因嫁了個混蛋丈夫被休回母家,后郁郁早逝,但因那時商隱年齡太小,二姐的這段婚姻悲劇在他幼年并未留下什么特殊記憶乃至傷痛。總的來說商隱還是有一個令大多數人羨慕的,比較幸福,至少是比較平順的童年。這一切,離他后來的“悲劇”性格是那么遙遠。
然而命運像一個老謀深算、殘酷狡猾的魔鬼,當你無憂無慮地沉浸在幸福之中時,他卻悄悄向你舉起了屠刀。唐穆宗長慶元年,商隱十歲,父親李嗣在浙西觀察使幕突然去世,這是詩人在坎坷的人生路上經歷的第一次重大打擊。父親在時,官職雖不高,但有穩定收入,一家人雖不十分富有,也算小康之家。現在家中的頂梁柱突然倒了,唯一的生活來源沒了,官宦人家少爺的商隱一下被拋到社會最底層。十歲的商隱和母親、徐氏三姐、弟弟羲叟一同護送著父親靈柩,從江南千里迢迢,一路歷盡艱難困苦,像逃荒的難民般狼狽地趕至鄭州將父親安葬。商隱家并沒有什么土地,為父親辦喪事又花去了家中僅有的一些積蓄,此時家已一貧如洗了。我總覺得,一個人不應長期盤踞高位,那樣看不到下層生活的艱辛,未免輕浮狂傲,也不可久沉淪下僚,那樣未免氣度狹小,不可能造就更高深的見解與開闊的胸懷。只有上上下下都經歷一番,人生各種況味都品嘗過,才會獲得一種關于人生的獨特目光,特別是經歷變故,從高端一下跌到底層,又有一顆善于捕捉的敏感心靈的人。父親的死讓少年李商隱經歷了一場強烈的心靈地震,從此一個單純的不識愁滋味的官家少爺開始真正品味到人生這杯滋味復雜時時變幻的酒,雖不情愿卻也必然感受到人情冷暖、世態炎涼。這種狀況,后來的曹雪芹、魯迅也都經歷過,也都對他們的文學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商隱的曾祖父、祖父都英年早逝,現在父親也步先人的后塵,拋下孤兒寡母去了。“古人常嘆知己少,況我淪踐艱虞多。”這種接連三代寡孤的身世,如宿命般死死地纏繞著李家,留給孤兒寡母是經濟上,更是心理上的巨大壓力。對漂忽不定、難以把握的前途命運的忐忑渺茫;在人前言行小心翼翼的屈辱自卑;壓抑、孤單、無助。所以這種家庭的孩子較之常人對幫助提攜過自己的知遇之恩,對親情、友情、愛情這些人生中溫暖情誼格外珍重,這是沒經歷過此的人所不能理解的。
可是眼前怎么辦?商隱雖幼,也是長子,他必須挑起養家的重擔。可一個孩子又能干什么?這進我們在關于李商隱的傳記資料時看到一個詞:“傭書販舂”。傭書就是為官家抄書,這不難理解,這時當時那些窮困的讀書人維持生計的一種傳統手段。販舂是指買進谷物舂米稍作加工后出售。這個活計,不但“低賤”,且收入微薄。但為了一家生計,商隱不能再挑三揀四了。
這時商隱家碰到了一個好人。就是商隱的一個遠房堂叔。商隱現在雖然家境艱難,但對于他這樣一個詩書之家,無論眼下處境如何困窘,通過求學讀書以圖仕進,仍是他必須堅持的唯一道路。因為只有這條道路才有可能令少年商隱改變自己的人生,重新振興家門。這位剛從淮海回來的堂叔就成了渴求學習的商隱的老師。
這位堂叔在當時那一帶是位響當當的名士,其人不僅博學多才,學養深厚,尤為難得的是,在當時那個人人爭奔仕途的社會,堂叔卻棄功名如弊屣,拒絕參加親友們勸薦的任何科舉考試,韜光養晦,孤介自守,只在家治家,教授商隱和弟弟堂弟這些晚輩,絕不附庸風雅,隨波逐流,顯現出與一般名士不同的節概。
這位長輩兼老師的堂叔對少年商隱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他不但傳授商隱兄弟傳統的儒家經典教育,使商隱打下一個很堅實的治學從文基礎,他耿直狷介的個性也令商隱強烈地感受到并影響了商隱以后的為人處世。商隱后來在任弘農縣尉時因發覺縣獄內冤犯很多,主張將他們寬釋,因此觸犯了頂頭上司,憤而辭職,并作詩發出“卻羨卞和雙刖足,一生無復沒階趨”的激憤之音。這與人們通常印象中那個軟弱、內向、卑下、庸俗的李商隱是多么大的反差!雖然家庭的責任與期望讓商隱不可能像堂叔一樣灑脫地“韜光不耀”,不求仕進,但這思想行為背后那種對權勢,對庸俗社會的蔑棄與不屑,那種堅挺的風骨,還是深深地根植進了商隱的體內,盡管很長時間幾乎沒有什么人能發覺這點,理解這點。
商隱在跟堂叔求學期間,受到古體詩文方面嚴格訓練,還閱讀了大量儒家典籍以及史部、子部、集部等重要著作。他如饑似渴地學習吸收著這些前人遺留下的經典精華,他一定是下了很大功夫,所以他后來作詩用典才會那么嫻熟、巧妙,信手拈來,自然貼切。這種有時似有賣弄之嫌的用典過多甚至成了商隱詩作的一個毛病,但他還是樂此不疲。他最喜歡杜甫、李賀的詩和韓愈的文章。這三位作家成了初試文才的商隱這一時期主要的摸仿學習對象。特別是命運與商隱有幾分相似的李賀。李賀也是父親早亡,文名早著,才華蓋世。以他當時的詩名、才華,加之朝中高官韓愈的舉薦,本該青云直上,在仕途中占有一席之地。李賀的父親名諱“晉肅”,恰與進士諧音。于是便有一些妒賢嫉能的小人趁機毀謗中傷,說李賀應避父名諱,不應參加進士之舉。這些言論今天看似無聊且荒唐,但在當時影響極大。在強大的輿論壓力面前,縱有一身才學與抱負的李賀最終被迫放棄考試,其后一生窮困潦倒,將畢生心血化作一篇篇泣血的詩篇,最后血干淚盡,27歲便如流星般隕滅了。李賀才高命蹇的境遇和詭麗奇幻的詩篇讓少年商隱無比動容。他不知道造化為什么這樣殘酷,榨干李賀的所有才華、所有血淚、所有真情后,讓一代才子早早黯然離世。燭光下的商隱眼睛模糊了。他不光是為這個從未見過面神交的詩人悲傷,似乎他還隱隱有種預感,自己今后的命運可能也逃不掉這樣嚴酷的煎熬與磨難!那時商隱大概只有十四五歲。
李商隱是敏感的,三代寡孤的身世、少年的不幸遭遇使他的內心如一件精美的工藝品,透明、純凈、脆弱易碎,但是再無暇的心靈最終還是要踏入社會。社會不像家中那樣,雖清貧,但總歸是單純的、溫馨的。對于既將踏入的這個他尚不熟悉的社會,商隱的內心有一種本能的既期望企盼,又防御、抵觸、不安的矛盾心理。這種心理,在他少年時離家出游,在某顯貴的席間有感寫下《初食筍呈座中客》一詩中,充分表露了出來。
嫩籜香苞初出林,於陵論階重如金。
皇都陸海應無數,忍剪凌云一寸心!
在詩中商隱將自己喻為初出林的嫩筍,有“凌云”之志。可是最后一句讓人看了十分壓抑難受。這顆嫩筍剛冒出嫩芽,還未生長壯大,更別說造福世人,就被慘遭剪伐。多么不幸,還未踏入社會、敏感的商隱,已給自己渺茫的未來設了一個很不祥的預言。更不幸的是,后來的經歷表明,他的這些預言,竟然都如讖語般毫不留情地應驗了,甚至比他想的還要冷酷、絕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