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校友楊佳:你怎樣,中國便怎樣
本期對話全國三八紅旗手標兵、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楊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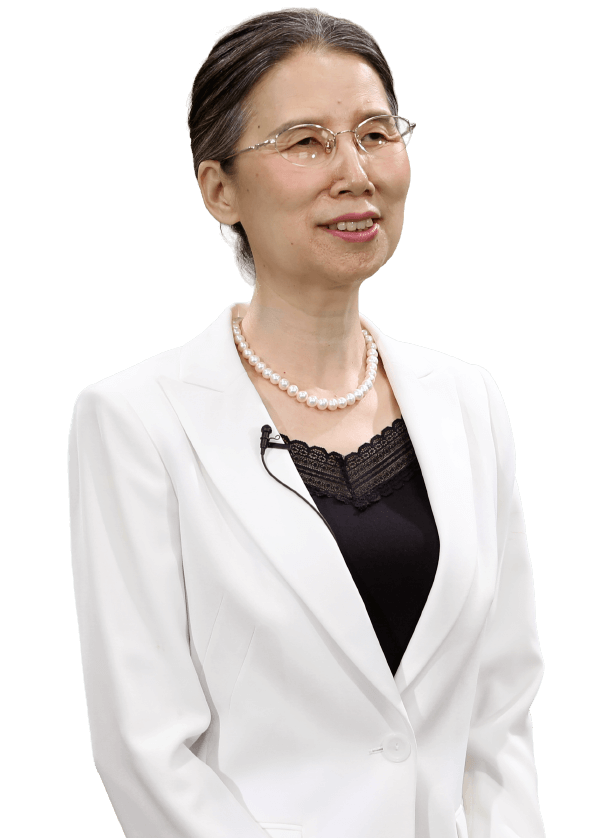

記者:四十年前,您在做什么?
楊佳:四十年前我還是個中學生。那是1978年,我在湖南師大附中讀高一,當時是理科實驗班的學習委員和英語課代表。
記者:您那個時候學習就這么好,理科實驗班還是課代表。
楊佳:對。那一年有兩篇文章可以說影響了我們這一代人,一個是郭沫若的《科學的春天》,還有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從小我和我的同學就非常崇拜科學家,要說有什么愿望,就是一個愿望:長大了要當科學家。
記者:那您高考的時候報考志愿跟科學相關嗎?
楊佳:高考實際上,當時倒沒有,高考就是為了感受一下考場是什么樣的感覺。因為我那時候是高一,我那一年不應該是高考,但因為成績好,在中學生數學和英語競賽里面都取得了好成績,名列前茅,所以學校就推薦我去試試,當時也沒多想,試試就試試唄,沒想到一試就考上了。
記者:那一年您多少歲?
楊佳:那一年我15歲。
記者:大學生活對您來說過得怎么樣?
楊佳:覺得非常充實。我記得當時是穿著一件印著“Spring of Science(科學的春天)”的襯衫走進大學校園的。我們1977、1978級的,因為就差半年,所以在一起,但是我們有個特點,就是年齡相差很大,像我們同宿舍的一位同學,她的哥哥也考上這所大學了。同學里面有兄妹,有夫妻,有的是屬于父與子這個輩分的,當時我考上大學的時候,就是我和我的班主任同時考上的。
記者:您跟您高中的班主任同時考上大學?
楊佳:對,高中的班主任,還有我們的美術老師,也是同時考上的,他考上了中央美院。所以就是這樣,師生關系都有,但是大家最主要都有一個特點,就是一種特別強烈的使命感和緊迫感。當時有句口號“把失去的十年奪回來”,這是我們國家積淀了十年的精英。
記者:那您覺得您用這四年時間把這十年奪回來了嗎?
楊佳:我跟大家一樣,奪回來了,盡管是年紀最小。我記得當時宿舍有規定,晚上9點鐘熄燈,就拉閘了。我睡上鋪,半夜醒來發現還有燈光,原來下鋪的一位同學是頭上戴著一頂礦工帽,在那兒聚精會神地看書。這種精神感染著我,在這種環境下,你不可能不用功,也不敢懈怠。最后就是這樣,我成了年紀最小的少年大學生,也是成績最好的。
記者:是,環境造就了一個人。19歲您畢業了,留校任教當老師,您是最年輕的學生,同時也是最年輕的講師,那您覺得這兩個“最”,和我們改革開放這個大環境有沒有什么必然的聯系?
楊佳:當然有了。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我的今天,也就沒有我從一個高一的學生成為一個大學生這樣的轉變。另外,改革開放的確給了我們這么一個機會。我一畢業留校任教時是19歲,去參加高考閱卷的經歷很有意思。那是在開封,是現在的河南大學,高考閱卷是7月份,天很熱,我扎了個馬尾,穿了條花裙子,就那么興高采烈地去報到了,沒想到門衛一下子就攔住了,操著開封話說:“回去吧,回去吧,現在不讓查分。”
記者:不讓查分,把你當學生了。
楊佳:把我當學生了。好說歹說他就不放行,幸虧我的同事及時趕到,說:“讓她進去吧,我們是一塊的,她也是閱卷老師。”就這樣才讓我進門了。我進了門以后,還聽他在那兒自言自語:“這是咋回事咧。”我現在想起來都挺好笑的,因為可能怎么看我都像是一個考生,而不像一個閱卷的老師。
記者:從小到大您的這些成績,換現在來說就是“別人家的孩子”。您覺得這跟父母的影響有什么樣的關系呢?
楊佳:我父母也是老師,原來在我們家的書架上就有一本書,那個名字就叫《課堂的藝術》,我記得封面就是一幅臘梅國畫,我很高興能當上老師,有這么一個平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跟自己最好的老師,還有最好的學生在一起。
記者:我們知道之后您的生活突然出現了一些變故,身體出現了狀況。當時是一個什么樣的情況呢?
楊佳:當時上課時讀課文,老是讀錯行,到后來書上的詞就變得越來越模糊。然后更可怕的是視力不行了,視野也變得越來越窄,可以說像舞臺的大幕就慢慢地往中心合攏。
記者:那個時候對您情緒上有什么變化嗎?
楊佳:當時以為不會很嚴重,換一副眼鏡就可以了,后來去同仁醫院檢查。
記者:當時醫生怎么講?
楊佳:醫生沒跟我說什么,但是跟我父親說了。
記者:父親瞞著您了嗎?
楊佳:對,我父親一夜白頭。父親當時問醫生有什么藥可以開,但那天什么藥都沒拿到,就是一通檢查,然后他什么也沒說。后來我才知道,我得的是視網膜色素變性,是一種罕見病,失明將不可逆轉,這是很難接受的,所以只能希望還可以治好,西醫不行看中醫。
記者:都去嘗試。
楊佳:對,還有針灸,還有一種是最痛苦的,就是“球后注射”,都嘗試過了,可是都無濟于事。“球后注射”是一個很長很長的針,你必須看,眼睛目不轉睛地。此后,視力一天不如一天,我記得我新辦好的國家圖書館的借書證遞到手中的時候,我已經看不清自己的相片了,就這樣,終于有一天,那是一個冬天的早晨,我睜開眼睛后是一片漆黑。
記者:您剛才用了“終于”兩個字,您是之前就有想過這樣一個最壞的結果嗎?
楊佳:我知道會有兩種結果,要么治好,要么失明,只希望這一天來得慢一點。回想起來,當年我的光明世界,那段二十九年的光明,是最美好的。我至今也忘不了藍天白云、綠水青山,還有父親的神采、母親的笑容,這對我來說都成了最美好的回憶。
記者:您失明之后,父親和母親還一直鼓勵著您,陪伴著您,給您最大的支持。我記得有一次采訪當中,記者問到您父親,說當時得知您生病之后他是什么感受?當時您父親做了一個比喻,他淡淡地說了一句“我就是她的拐杖”,然后一下子鏡頭掃到了您,能看到您眼眶濕潤了。您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當時您聽到父親這句話的時候,內心活動是什么樣的嗎?
楊佳:是,當時我熱淚盈眶。因為家人總是在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或者最困難的時候出現。失明以后,伴隨而來的還有婚姻家庭的破裂,這時候我感受到做殘疾人的艱難,而殘疾女性更難,盲人又是殘中之殘。
記者:這個時候您覺得家人對您來說意味著什么?
楊佳:那就是最溫馨的港灣。當時有人就說,我就像汪洋中的一條船,有家人的陪伴,不離不棄。我很少跟他們說自己的感受,比如說有一次我坐公交車,有人提醒我說那兒有個座,我一動不動站在原地拼命地想,他說的那兒到底是哪兒?再往下就不太敢講了。因為一個生活中連這兒、那兒都分不清的人,那他生命的位置又在哪兒?
記者:您剛才講的這些,我覺得對任何一個人都是不可想象的困難,但是我發現您在講述的時候嘴角依然上揚,云淡風清,好像沒有什么,我覺得這是您最寶貴的品質之一,在遇到所有困難和挫折的時候,您都覺得一定會戰勝它,所有的困難都會過去。
楊佳:現在回頭看可以這樣,當時的確非常艱難。一切從頭開始,要像個小孩,在父母的幫助下一步步學穿衣、學吃飯、學走路。我是用盲杖探路,走著走著把自己給絆倒了。大熱天,用吸管喝飲料,一低頭,吸管戳傷了眼睛,所以現在戴著眼鏡。
記者:你是為了保護眼睛?
楊佳:為了保護眼睛。但是從不戴墨鏡,是因為還想留住跟大家,跟每個人交流的一個目光。
記者:我曾經在網上看過一個帖子,說您的學生上您的課,快半個學期了,還不知道您是個盲人。這就說明其實您的狀態非常好,大家根本看不出來您有什么不一樣的地方。但是對于像我們不了解情況的人就覺得很好奇,您上課需要板書,這是怎么完成的?怎樣讓同學們看不出來您身體的異常呢?
楊佳:為了做到這一點,我的確是做了很多的準備工作。上課重返講臺的確是我的一個心愿,這個時候就是父親說過的“爸爸給你當拐杖”。所以失明這么多年,幾千個日日夜夜,我就緊緊地握著父親的手臂坐公交,擠地鐵,輾轉到教學樓。早上8點我會在教室里準時迎候我的學生,他們不會知道,為了不遲到我跟父親不到6點就出門了,剛才提到的那個板書,學生不會知道我緊貼黑板的左手是在悄悄丈量尺寸,還有這個腳步也是這樣幫著丈量尺寸。
記者:您右手在寫板書,左手要去量它的尺寸,左右距離,保證這個板書漂亮、好看、準確。
楊佳:對,還有整個黑板大概有多長、多寬。
記者:這個您都要在開課之前把它量清楚。
楊佳:對,事先都要做到心中有數,而且事先板書寫好。在課堂上,當然也會寫,所以這方面都要知道哪些地方有空隙什么的。當然也采用多媒體教學,但學生不會知道這個觸摸屏被我貼上了一塊、一塊的膠布來做記號。剛才說學生有的上了半個學期的課才知道,因為我上課就是上課,我不會講其他的與課程無關的東西。有一次,學生發現我眼睛看不見,是因為劉恒采訪我,來聽我的課,所以后來在《北京日報》寫了一篇報告文學《小楊教書》,劉恒說聽楊佳老師講課是一種美的享受。
記者:真好。聽您這樣講了之后,我特別想去上一堂您的課,希望以后有機會能坐在您的課堂里,認認真真聽一節課。
楊佳:歡迎。
記者:我們再來聊2000年,相信談到這一年,您的整個情緒就會變得非常高漲了,因為這一年您迎來了人生當中的一件大喜事,您拿到了一份來自哈佛的offer(錄取通知書)。
楊佳:是,這也是我失明以后第8年。在新的世紀里,我所在的研究生院提出了新的奮斗目標,就是要創建國際知名、亞洲一流的院所,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在這種目標的感召下,我又萌生了一個念頭:我還想讀書。
記者:可是那時候,您已經大概37歲了。
楊佳:對。
記者:37歲選擇再次到美國去讀書,當時怎么想的?
楊佳:挑戰自我。
記者:繼續挑戰。
楊佳:對。這個時候讀書就跟我當時1978年考大學不一樣了,目標變得更明確。
記者:這不是輕輕松松試一下就能考上的。
楊佳:我就報考了一個學校,所以當時想著,要上就上最好的學校,一流大學,要學就學最新的專業,結果就這樣了,被哈佛大學錄取,而且學的又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公共管理碩士學位。
記者:對,那個時候在國內還沒有這個專業。
楊佳:沒有。2000年,我在聯合國參加千年論壇的時候,當時專門有個專題,就是全球化,在這里我就覺得我需要學更多的知識,因為對這些方面有的國家是褒貶不一。但是對中國來說,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這就是為什么報考哈佛,而且學公共管理碩士學位。這個學位可以說是比博士學位的含金量還大。
記者:更難拿到?
楊佳:對,因為學完以后可以學以致用。哈佛老師上課很活,要求很高,而且是案例教學。我記得微觀經濟學第一堂課,老師就往黑板上掛了三張圖:這是里根時期的經濟、這是克林頓時期的經濟、這是布什時期的經濟,而且那個圖上面是用紅黃藍的筆,畫了很多道道,同學們看的是一目了然,我恰好相反。
記者:那怎么辦呢?
楊佳:我一臉茫然,只能課后用功了。另外,哈佛老師上課從不照本宣科,學生全憑筆記。我用學校提供的特殊鍵盤,每上一堂課就按下一個開關鍵,身旁的同學會提醒我工作鍵的指示燈亮了,這個時候我會隨著老師的講課熟練地打起字來,一堂課下來,同學們會說楊佳的筆記就是一篇完整的講義。哈佛有一個特點,閱讀量特別大,每個老師貌似把自己的那門課當成唯一的一門課一樣,每一堂課它的閱讀量都不下500頁,同學們感覺時間不夠用,對我來說更不夠了。因為我多了一道程序,首先要通過掃描儀把講義一頁頁掃到電腦上,再通過特殊的語音軟件,把內容讀出來,這么一來時間全沒了,只有拼速度。我由原來每分鐘聽200多個英文單詞提速到400個。
記者:每分鐘400個英文單詞。
楊佳:對。這可以說幾乎就是錄音機,快進式,變了調的語速,就這樣差不多每天學習到凌晨兩三點,不僅完成了學校規定的學習任務,還超出了學校規定的,多學了三門課。我記得第一個學期,我填選修課程的時候,我們的項目負責人還直說“天啊,天啊”。
記者:不相信你能完成是嗎?
楊佳:對,不相信我能完成。等到第二個學期,我把自己要學的課程報上來的時候,他就不是一臉質疑了。在哈佛,要追隨大師。像我學了Joseph Nye全球化的課程,還有我的論文,就是《論鄧小平的領導藝術》,被肯尼迪學院定為范文。教領導藝術課的正好是哈佛的頂尖教授,也是哈佛公共領導中心的主任,30歲入白宮效力過四位美國總統(尼克松、福特、里根、克林頓),包括民主黨和共和黨,這個頂尖教授叫David Grogan,他為我贈書題詞,他扉頁上寫了滿滿的一版,上來就說:“佳,你教給了我們更多的東西。”而且他的那個學期最后一堂課還請我做總結發言,他為我破例打了哈佛最高分A+。
記者:A+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大概一年會有幾個人會拿到?
楊佳:沒有人。因為哈佛肯尼迪學院教務處規定,教授給學生課程打的最高分只能是A,Grogan說不管那么多,打了A+。這是教授對我的一種肯定,最令人難忘的就是哈佛畢業典禮,我從Joseph Nye手中接過畢業證書。
記者:還記得那一刻當時心中是什么樣的感受嗎?
楊佳:當時Joseph Nye喜氣洋洋地跟我說:“Congratulations Jia,You are China's Soft Power,Goodluck(祝賀你,佳,你是中國的軟實力,祝你好運).”
記者:這個評價太高了,中國的軟實力。
楊佳:對。當時全場幾千名師生自發起立,為我,也就是哈佛建校300多年來第一位獲MPA學位的外國盲人鼓掌歡呼。
記者:聽到這里,我也禁不住想為您鼓掌了,真的太棒了。
楊佳:所以那一刻覺得非常激動,無比自豪。
記者:您是哈佛的驕傲,也是所有中國人的驕傲。我們也要感謝您,您走出了國門,讓大家看到了中國人的文明素質和整個國家的文明程度。
楊佳:我覺得是作為改革開放的一員吧,能夠做到這樣一點。改革開放的確是讓我能夠放飛夢想,能夠重返講臺,能夠繼續教書、寫書、讀書,從哈佛回來能夠學以致用。我能成為全國政協委員中唯一的一位盲人女性,并且在三年前,在人民大會堂代表九三學社做了題為《點贊正能量 厚愛正能量 弘揚正能量》的發言,“強大的正能量源自每一個人,你怎樣中國便怎樣,中國怎樣你才會怎樣”,這不正是改革開放中國精神的生動寫照嗎?
記者:是。“你怎樣中國便是怎樣”,這句話非常有力量,當時說出來之后,在網上也引發了很多反響,大家紛紛為您的這一篇演講點贊,同時有很多人為這句話點贊,覺得您說出了所有中國時代新人的心聲。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的時候也提出了要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而我們知道您現在身上有很多的職務,而更重要的您還是一位教書育人的老師,那么對于培養時代新人,這方面您有什么感悟?
楊佳:我覺得作為老師,這是我們的責任。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才是春,我們的確是需要人才,正好我所在的中國科學院大學也是一個人才培養的基地,也是一個高地,在這里我們能夠勇攀世界高峰,能夠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奉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就這點而言,教師是一個非常光榮的崗位。
記者:我們也知道現在很多人都把您當成是人生的榜樣、楷模和勵志女神,在您的人生當中有沒有這樣的一個人一直激勵著您前進?
楊佳:有啊,我的這個女神,這個楷模,就是我的導師李佩先生,而且她一直激勵著我,她是被譽為“中國應用語言學界第一人”,也是“中關村最美的玫瑰”。為了建設新中國,舉家回國,她的丈夫郭永懷是美國貝爾實驗室的著名科學家,為我們國家成功研制“兩彈一星”殫精竭慮,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在飛機失事的一剎那,他跟警衛員緊緊地抱在一起,這是一個將生命置之度外的壯舉。就是這么一個舉動,夾在兩個人身體之間的絕密文件才得以完好無損,可兩個人的身體再也無法分開,只能合葬。唯一的女兒郭芹,也被病魔奪走了生命,一家三口就剩下李老師一個人。可她還在教學,還在教博士生,下雪天還在義務給博士生補課。所以在我生命最茫然、最黑暗的時候,我想到了李先生,我想是什么力量在支撐著她,導師的崇高信念跟人格風范激勵了我,給我巨大的勇氣和力量。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天生我材必有用,只要活著,就應該活出尊嚴,活出希望,更活出愛,這就是李老師教給我的。我也堅信,海倫·凱勒說:“假如給我三天光明。”要我呢,我不滿足“假如給我三天光明”,我想要給我的話,那給什么呢?我對未來是充滿信心的。因為我堅信,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有基因療法、干細胞研究領域的這些重大突破,我相信盲人總有一天會重見光明。
記者:我們也共同祝福您,祝福大家都能夠勇敢地去面對生活,努力去愛,同時勇敢的去面對挑戰,面對困難,相信陽光總在風雨后,謝謝您楊老師。(本期嘉賓由全國婦聯宣傳部推薦 記者:范曼瑜 攝像:高晟寒 趙洋 編導/剪輯:林和 監制:劉鯤鵬 責任編輯:鄧植尹)









